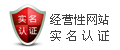《野望》:传统的重量与时代的引力
在百年现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之中,乡土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新文学发轫之初,鲁迅、茅盾、沈从文等文学大家即以不同的视角和笔法奉上经典之作,不仅引领乡土叙事之风,也为新文学整体发展奠定了历史基业。此后中国文学的浩荡百年路,革命、救亡、建设、改革在不同时期交替而为叙事的“主旋律”,但乡土叙事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始终活跃,并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经典谱系。
然而,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叙事面临着新的考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拓进,当代中国乡村正处于剧烈的现代转型之中,如何书写这种正在进行的“山乡巨变”,如何讲述其中的中国故事,如何表现“内在于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是考验当代作家的严峻课题。与此同时,作家队伍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当下仍然在从事乡土文学创作而成果显赫的作家……大都是‘50后’‘60后’,他们的乡村生活经验,是以1950—1970年代为主要时段,尽管作家们通过不断地返乡观察和思考21世纪乡村的新现实,但是其与当下乡村生活的隔膜和内在的力不从心不必讳言”[1],这一代作家的乡村经验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另一方面,青年一代作家更多地在城市文化背景中成长,更多致力于城市文学写作。双重变化衍生的共同后果就是当下乡土写作如何赓续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付秀莹的出现及其创作别具意义,她的以《爱情到处流传》《陌上》为代表的系列乡土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并以极具辨识度的叙事风格迅速赢得广泛关注,成为当下乡土书写的重要力量。
《野望》是付秀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继《陌上》之后又一部聚焦乡土中国的力作。在经历了《他乡》的“出走”之后,这部作品的叙事焦点再度返归“芳村”,接续了《陌上》对于“芳村”的正向的、微观的聚焦和呈现,讲述了“芳村”在新时代的故事,呈现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的世态、情态与状态。《野望》要处理的核心命题,仍是现代性背景之下中国当代乡村的现时状态和未来可能问题。作为有着厚重文化传统和历史根基的当代乡村,正经历着深刻的现代转型。这个过程一方面体现在经济层面由农业而至工业的模式转型;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层面的一种结构和秩序的重组,是对以往自身文化传统的改造和重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性的变化,才能真正迎来一个新的现代主体。《野望》与《陌上》一样,都是聚焦和展现这种运动中的、过程性的复杂状态,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之中,从细部和内部来展现这一历史过程。在叙事方式上,《野望》延续了《陌上》以日常生活叙事统摄整体结构的方式,将人物置于重复、循环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行表现。同时亦以群像式女性人物为主体,承担起讲述乡村故事的叙事任务。但与《陌上》相比,《野望》呈现出更为积极的通过个体故事和乡村变化来折射时代进程的努力,在写出转型期乡村秩序稳固恒常一面的同时,也写出了时代引力所召唤出的一些新的价值趋向和可能的未来图景,“芳村”内部有了更多对于时代的共鸣和回响,有了更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
一、传统的重量:节气、风俗与共同体
付秀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节气或重要节日。比如在《陌上》开端的“楔子”中,她就直言:“芳村这地方,最讲究节气。”[2]之后,她从过年开始,详细介绍了正月初五、正月初十、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二月二、寒食节、端午节、鬼节、八月十五等近乎一年的重要节日。在乡村,节气或者节日就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刻度,是比四季轮转交替更为具体的时间秩序。但是在付秀莹笔下,对于节气和节日的描写,不仅仅是为叙事设定一种时间结构,同时也是一种具体的叙事内容。她往往以节气、节日为切入点,细腻书写节气、节日背后所对应的颇具地方特色的风俗文化。比如正月十六游百病、二月二送新鞋,等等。因此,节气、节日在付秀莹小说中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符号,也通过与风俗文化的合体而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内容。
长篇新作《野望》在叙事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延续了这样一种叙事路径,并将节气、节日的叙事地位推进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在结构上,《野望》以二十四节气为经络,贯穿起文本整体,每个章节均以一个节气命名,以“小寒”起笔,至“冬至”终结。二十四个章节按照二十四节气的自然顺序一一对应,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闭环。也就是说,小说顺时写了一个自然年内的“芳村”故事。从时间长度来说,这样的时间跨度似乎很难写出某种革命性的变动来,但付秀莹写作的一个整体性特征是其写作主题的延续性,她的写作基本都围绕“芳村”展开,其内部的人物、故事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和内在一致性。比如《野望》中的人物几乎都在《陌上》中出场过,而且人物的身份、故事高度一致,这就使得两部作品之间具有深度互文关系。因此,虽然看似时间跨度并不长,但由于作品之间的这种特殊的互文关系,在前后对照之中,《野望》中的“芳村”的变化仍然清晰可见,甚至可以说是剧烈的。
在内容上,在每一个章节内部,都发生着与这一节气或节日有关的故事,节气及其所连接着的风俗习惯成为故事的重要元素。比如《冬至》这一章里的故事与吃饺子相关,《清明》一章中的故事与上坟关联。小说形成了这样一种内在结构:节气—风俗—故事。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行走在具有秩序性的节气风俗之中,根据节气风俗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节气风俗在不同的人物故事中凸显出一种稳定性。在这种结构之中,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被包裹在浓浓的地方性的文化风俗之中,获得了浓郁的地域色彩。
但描写风俗不仅仅是为了展示一种文化风景,而是通过风俗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呈现一个有着共同文化理念和精神信仰的乡村共同体。风俗是特定区域、特定人群中“长期形成的风气、礼节、习惯等的总和”[3]。在风俗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特定区域的人群既是生产主体,也是实践主体。风俗需在人这个主体之上才能显影其存在和影响力。反过来,人又受风俗习惯的制约,影响着个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规范。因此,风俗与乡村民众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的关系。借助于风俗与内在于乡村之人的这种关系,付秀莹勾勒出一个有着相近的生活习惯、道德理念甚至精神信仰的乡村共同体,而节气、节日与风俗,正以其强大的稳固性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和象征功能。
付秀莹笔下的“芳村”是一个带有共同体特征的场域,其内部有着高度一致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精神信仰,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文化传统和内在秩序。这些在时间之中形成并沿袭下来的传统支撑且规范着乡村的日常生活。比如,共同的风俗习惯成为他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贯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根据节气或节日,自然而然地激活关于地方风俗的记忆并进行相关活动。而这些活动往往具有普遍性,在乡村内部可以相互呼应;再比如相近的道德原则和生活观念。面对溢出传统乡村道德范畴的情感关系、赌博等不良行为,会唤起一种集体的道德谴责和批判。当有子因为赌博被扣留时,人们对于根莲的普遍同情体现了这种道德原则的集体性;再比如,精神信仰之中对于“神”的迷信。当人们遇到生活困境,都将小别扭媳妇视为最终的解决方案,这里尽管体现了乡村文化传统中蒙昧的一面,但行为的一致性同时也显现出一种共通性。因此,尽管付秀莹笔下的“芳村”人人都有一出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在更深层的文化精神质地上,却是一个高度同质的共同体,是一个典型的由乡村文化传统形塑出的稳定的历史主体。
在论及现代性时,英国学者鲍曼指出,“这个星球的每一片土地,除了鲜有的几个例外,都在顺应一场现今被称为‘现代化’的急切的、强迫性的、不可阻挡的变迁,并被迫接受与之俱来的一切事物”[4]。付秀莹笔下的“芳村”也不例外,她对于乡村共同体的观察和塑造也是置于现代性这一视野之下的。然而,“现代”与“传统”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传统是对一种模式或一种信仰的传承,是在世代延续更替中的传承:它意味着对某种权威的效忠和对某种根源的忠诚”。而现代往往伴随着“对新的迷信”,并且“现代的背叛”[5]这一悖论性的问题也交织在乡村的现代转型之中,在乡村内部,存在着两种力量的博弈,一种是源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的稳固性力量,另一种则是走向现代的变革性力量。可以说,乡村的现代化本质上正是两种力量对抗的过程和结果。付秀莹清晰地意识到乡村变化的这种复杂性,她认为,“时代巨变中,一些东西烟消云散了,一些东西在悄悄地重建。更有一些东西,中国乡土文化中积淀最深最厚的那一部分,依然在那里坚硬地存在着”[6]。变与不变的辩证构成了其乡土写作的基本观念和立场,也是其写作的两个主要面向。相比较而言,她更多写出了那些“坚硬地存在着的”不变的内容,对乡村共同体的塑造就是最大的显影机制和具象载体。
通过“芳村”这个共同体,付秀莹展现了深嵌在乡村内部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形塑的稳固的乡村结构和精神观念,“传统”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其自身的重量,它已然凝聚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和惯性,影响着乡村内在秩序和精神结构的生成和衍化。这种传统有多少鲍曼所言的可以“生物降解”[7]的成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将深刻影响当代乡村的现代转型。由此,作品触及了一个重要的现代命题:乡村的现代转型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盛充裕,同时意味着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改造和重建。唯有重组这个文化传统的密码,才可能真正完成现代转型。因为,乡村的转型最终要以内在于乡村共同体的人的转型来完成,也以内在于乡村的人的转型完成来作为标志,而人的重塑正是文化重塑的后果。付秀莹的“芳村”叙事呈现了这种重塑的复杂性以及难度。